本文聚焦全国两会后全国政协委员靳东关于“成立国家遗嘱库”的提案引发的热议,深入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下遗产纠纷问题,介绍了现有遗嘱库情况,还通过养老院老人咨询遗嘱的案例,展现了人们对遗嘱规划从避讳到理性的转变。
全国两会虽已落下帷幕,但两会上的诸多热议话题依旧热度不减。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靳东提出的“成立国家遗嘱库”提案格外引人注目。该提案凭借超亿次的关注量,成功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以及B站热搜榜榜首。
多平台的广泛热议,实则凸显了老龄化社会的核心痛点。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与之相伴的是遗产纠纷案件频繁发生。靳东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建立国家遗嘱库,这个遗嘱库可以像110一样逐渐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让老人了解这个遗嘱数据库,为法院处理有关问题提供支持。”他透露,这一建议的灵感源于自己参演的电视剧《底线》。为了演好剧中的法院立案庭庭长一角,靳东接触了大量案例,深刻目睹了因有无遗嘱、遗嘱能否顺利执行、遗产能否平稳分配而引发的各类纠纷矛盾。

受访者供图
“靳东的建议,在我们业内也引起了反响。”童丰说道。早在2013年,中国公证协会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全国公证遗嘱库的建成。尽管目前“国家遗嘱库”尚未建立,但在“公证遗嘱”方面,已经存在全国性数据互通的库。童丰认为:“不论国家遗嘱库是否会建立,老百姓对遗嘱这件事情的重视,是会减少很多身后事纠纷的。”
随着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对遗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一些公益性质的遗嘱服务机构应运而生。2013年,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正式启动,这是全国首个遗嘱库,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建有60余个分库。2016年,浙江民生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南都法律服务所、杭州市上城区家兴继承服务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设立的公益项目浙江遗嘱库开始运营,这也是浙江省首家遗嘱库。

叶世娟(左一)与咨询遗嘱的老人 受访者供图
养老院里的“生死课”:从避讳到理性规划
3月11日上午,76岁的吴老太和她妹妹走进了浙江遗嘱库的接待室。吴老太向工作人员问道:“我名下有两套房,今后想留给我的孙女,需要怎么操作啊?”
工作人员吕小燕并没有直接回答吴老太的问题,而是先为姐妹俩泡了两杯茶,然后关切地询问:“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有几个子女?他们对你孝顺吗?”
叶世娟解释说:“在浙江遗嘱库,立遗嘱之前,一定要详细了解家庭情况。”在与咨询者的聊天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探索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理清复杂的家庭、情感关系,这是立一份严谨遗嘱的必要条件。她还强调:“更多的时候,是要解心结。”
吴老太向吕小燕倾诉起自己的孩子:“我老伴去世早,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和我关系都很好。但是我的儿子,哎!”吴老太无奈地摇起了头,不愿多说,只是轻叹“不成器”。
原来,吴老太曾和女儿聊过去世后的遗产分配问题,女儿生活条件优渥,自愿放弃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我知道,她当姐姐的,是希望我把房子传给不宽裕的弟弟。”但吴老太担心遗产交到儿子手中后被败光,所以才想过来咨询一下,能否立遗嘱把房子都留给孙女。
在这间咨询室里,每天都有近20人敞开心扉,吐露心声。这些咨询者虽然经济条件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面对死亡。
叶世娟认为:“在与立遗嘱人的沟通中,我们帮助他们用遗产分配的形式,梳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在她看来,这是一堂非常有必要的“生死课”,是立遗嘱人坦然面对死亡时,需要直视的隐秘心事。
中华遗嘱库也有着类似的流程。中华遗嘱库江浙沪区域负责人黄海波介绍:“除此之外,在立遗嘱之后,我们还会为立遗嘱人拍摄‘情感录像’,让他们写下‘幸福留言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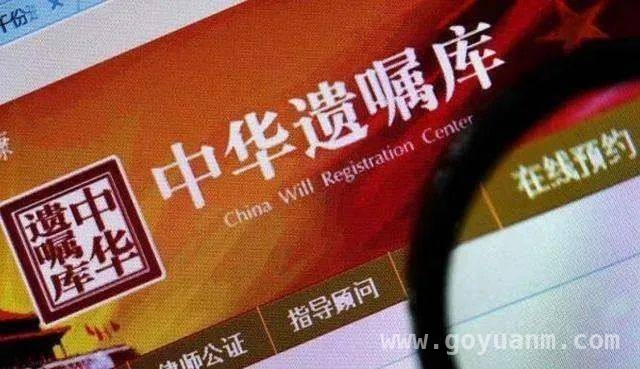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工作人员在养老机构现场办理遗嘱 受访者供图
童丰告诉记者:“每个月,我们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都会进入社区,为老年人宣传‘身后一件事’。”对于老年群体而言,遗嘱有没有必要立、财产应该怎么处分、希望留下怎样的“生前预嘱”,都应该在有判断力、思考力时考虑清楚。在童丰看来,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而且,这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中年人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当更多人开始讨论遗嘱与‘身后一件事’,本质上是在追问,如何让生命的谢幕少些遗憾,多些温情?”关于成立国家遗嘱库提案的热议,或许正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年人开始代入立遗嘱的视角,从而审视自己的财富与亲情,当生死议题不再被遮蔽,每一份“身后事”的从容规划,都将为生者注入更多温暖与力量。
本文围绕靳东“成立国家遗嘱库”的提案展开,指出该提案反映了老龄化社会遗产纠纷的痛点。介绍了现有公证遗嘱库和公益遗嘱库的情况,并通过养老院老人咨询遗嘱的案例,展现了人们对遗嘱规划态度的转变。强调遗嘱规划不仅能减少遗产纠纷,还能帮助人们梳理亲情关系,从容面对生死,体现了社会的成熟与进步。




